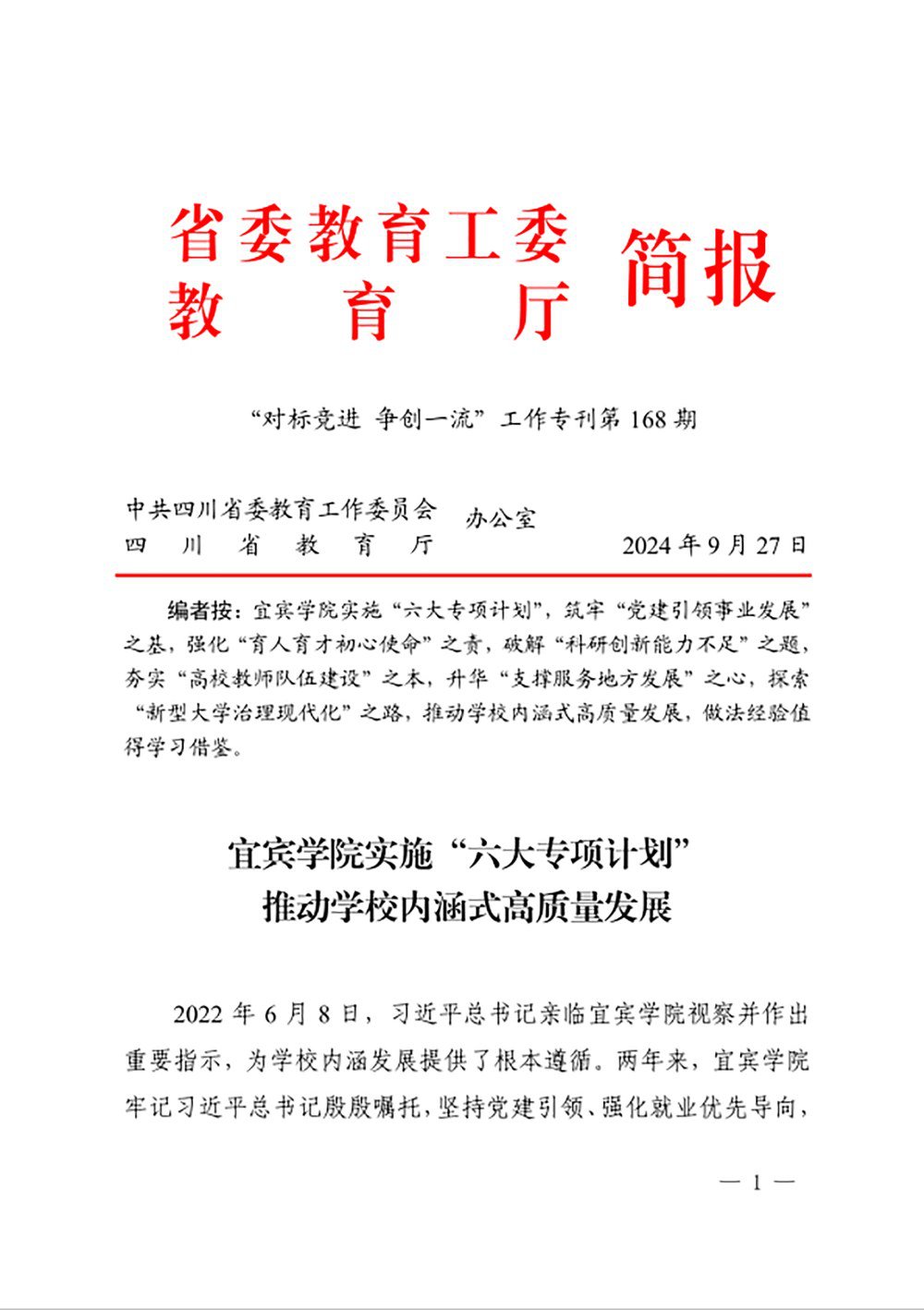要論我這半輩子吃得最多的菜,粗算起來,當屬咸菜。
俗話說:南甜北咸,東辣西酸。這北方的咸,除了指炒菜的口味外,還要說咸菜。北方人愛吃咸菜,這應當是由自然氣候特點而形成的生活習慣,祖輩流傳,沿襲下來。
干旱少雨的北方,冬季漫長,適合蔬菜生長的季節(jié)短。在沒有塑料保溫大棚的年代,交通也不便利,只能靠天吃菜,主要是土豆、圓蔥、白菜、蘿卜等少數(shù)能存儲的菜。人們用鹽腌制一些菜,以圖長久存放。這就是咸菜的來歷。人們賴以生存的咸菜,不知是哪位巧婦發(fā)明的,歷史上,這事兒不像倉頡造字那般影響重大,沒有專家去考證過它的起源,但它確實是與百姓們的一日三餐息息相關。
在我的家鄉(xiāng)沂蒙山區(qū),早先,腌咸菜是農家一年當中的大事,莊戶人家就地取材,各顯其能。春天上市的香椿芽,秋后收下的胡蘿卜、青蘿卜、辣菜疙瘩、辣椒都是用來腌制咸菜的好材料,其中尤以辣菜疙瘩最為普遍。
辣菜疙瘩,通常是用來腌咸菜的。但它也可以做菜蔬,做法是切絲輕炒,加適量食醋,密封燜起來,俗名“燜辣菜”,聞起來刺鼻,類似芥末的味道,吃起來會嗆出眼淚,十分過癮,這是我奶奶的“看家菜”。
將辣菜疙瘩去葉子、毛須及根部,洗凈晾干,裝入專用的咸菜缸里,層層撒上大鹽,用往年的老咸菜湯,再添加清水,沒過辣菜疙瘩即可,或再添加少許鹵水和花椒。幾個月后,待辣疙瘩通身變成醬土色,便可食用了。人口多的人家,置一大缸,能腌上百斤辣疙瘩,可吃一年以上。腌制時間久的老咸菜更有味道。
條件好的人家,食用時還要再加工,或切絲烹炒,或配以蔥絲、香菜、醬油、香油涼拌。多數(shù)人家都是撈出疙瘩后切粗條即食。小的時候,每天清晨,我從被窩里爬出來,從娘的手里接過一個剛下鏊子的熱煎餅,順手捏一塊辣疙瘩咸菜就吃起來,若能卷上熱豆腐吃,那可真是美食了。山東名吃中的煎餅卷大蔥,其實還要有疙瘩咸菜配著吃,那才是正宗的。
腌制好的疙瘩咸菜,還有一個再加工辦法。村子里從前種植煙葉,生產(chǎn)隊里都有烤煙的專用房屋,俗稱“煙屋子”,就是一座土坯屋子,地面凹下一米多深,以土坯壘成一條條環(huán)形通道,通道連接外面的火爐,爐火燃起后,煙火穿過通道,最后通過煙筒排出,煙火在循環(huán)中升高了屋內的溫度。屋內當空上下橫著插滿一排排木檁條。黃煙收獲的季節(jié),人們將鮮煙葉左右均勻地捆扎在一條條秫秸桿子上,再手把手傳遞,掛到木檁條上。在烤煙的過程中,大家就把腌好的辣疙瘩擺在通道壁上。不幾天,煙葉由青變黃,手感焦脆,就該出屋了。期間,那些疙瘩咸菜也烤至軟熟,就像烤地瓜,卻是咸中帶香,軟綿可口,最適宜牙口不好的老人小孩。
咸菜是個大家族。
清明時節(jié),香椿芽長到一掌長短,采摘下來,先以粗鹽揉搓,晾干,擺入壇罐,層層加鹽,腌成后,香氣四溢。一手擎一支香椿芽咸菜,一手執(zhí)煎餅或饃饃,那香椿芽咸菜就像一支小小的樹苗,連枝帶葉,慢慢咬下,細嚼慢咽,一股清香縈繞齒唇。
秋天里,將韭菜花采下來,碾成韭花醬,還可以加入扁豆、生姜等腌制起來,也是一道味美的咸菜。
母親喜歡制作豆豉咸菜。秋后收下的大青蘿卜,切片備用,將黑豆煮熟發(fā)酵,佐以食鹽、花椒水等,與蘿卜混合裝入磁壇,密封月余,待蘿卜腌透,吃起來綿軟酥香,此品類似臨沂特產(chǎn)“八寶豆豉”,是家里咸菜中的上品。
我曾吃過蓖麻子腌制的咸菜。新鮮的蓖麻子,渾身毛茸茸的樣子,撥開毛皮,內含的蓖麻籽可榨油,腌透后連皮帶籽吃,也別有一番風味,但我已多年沒有見過這東西了。
沂蒙山區(qū)的小河溝眾多,秋后,有人就趁著夜色,點燃苘麻桿(代替稀有的手電筒),去摸螃蟹。那里的螃蟹沒有海蟹和南方的大閘蟹那般肥美,個頭也小,但可以用來腌制咸菜。備一博山磁壇,將新鮮的河蟹沉入冷卻的鹽水中,加上熟花生米,以大蔥、花椒配料,密封不久,即可食用。此品鮮香可口,端上一碟,可做招待賓客的酒肴。
小時候,聽說供銷社從海邊躉來了成簍的蝦醬,母親給我一只瓷碗,兩角錢,叫我去買一碗回來,配以大蔥或辣椒、雞蛋炒熟,那叫一個齁咸,也算是咸菜中的海味了。
紅艷的豆腐乳,各色的咸魚,尤其是白鱗魚,在那一分錢掰成兩瓣花的年代里,家里有公職人員的人家,手頭較寬裕,能挪出錢來買些,對家境一般的人家,那都是咸菜中的奢侈品呀。
貧窮的年代,每頓飯能有咸菜吃,也是很滿足的,在青黃不接的時候,咸菜也往往接續(xù)不上。記得我上中學的時候,一周回家一次,帶足了煎餅干糧,還要弄一罐頭瓶子,把辣疙瘩咸菜細刀切條裝瓶,倒些醬油,這就是一周的下飯菜了。遇上咸菜短缺,母親就去鄰家借一點,日子雖過得緊巴巴,上學的勁頭卻十足。
后來,考上大學,我第一次走出了沂蒙山,才慢慢知道了北京醬菜、東北泡菜、四川榨菜、福建蘿卜干、潮汕咸菜、延邊腌蕨菜、浙江梅干菜……全國各地都有自己的特色咸菜。
看過一則報道,說當年解放大軍進入大西南時,首先占領的,除了電廠、水廠等關系民生的重要部位之外,就是榨菜廠。因為,這關系到幾十萬大軍的飲食。咸菜里面也出戰(zhàn)斗力。
一方水土養(yǎng)一方菜。
榨菜長在南方,辣菜疙瘩據(jù)守北國,作為咸菜家族的兩大主力,割據(jù)一方,互不越界,否則就要變種。
還有一種菜不得不提,就是“雪里蕻”。詞典上說:一年生草本植物,芥菜的變種,葉子長圓形,有銳鋸齒及缺刻,花鮮黃色,種子褐色。雪天諸菜凍損,此菜獨青,故名。這廝是芥菜的變種,在全國各地有不同的名字,據(jù)說,保定叫春不老,重慶稱其香青菜,湖北也有地方叫做臘菜的。我的家鄉(xiāng)似乎沒有這品種。我在北京上大學的時候,同宿舍的同學從家里帶來炒雪里蕻咸菜,我總以為是蘿卜纓子做的,但口味的確不錯。
不知道中國是不是咸菜之鄉(xiāng),但中國的咸菜品類之多,制作手法之精,食用之普及,老外們是不能比的。咸菜應該算是一種重要的飲食文化。因為從地廣物阜、眾口不一的國情來看,咸菜在國人飲食方面還是占有一定地位的。并且,這老祖宗流傳下來的食物也許還要流傳下去。借用黑格爾老先生那句話:凡合理的都是存在的,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。咸菜,亦如是。
斗轉星移。如今,日子富裕了。但走過那段歲月的我,口味卻難改,還是喜歡來盤小咸菜下飯,不圖別的,可口,可胃,可心!
立冬時節(jié),黃葉飄零。正是腌咸菜的季節(jié)。眼前,總晃動著那辣菜疙瘩的影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