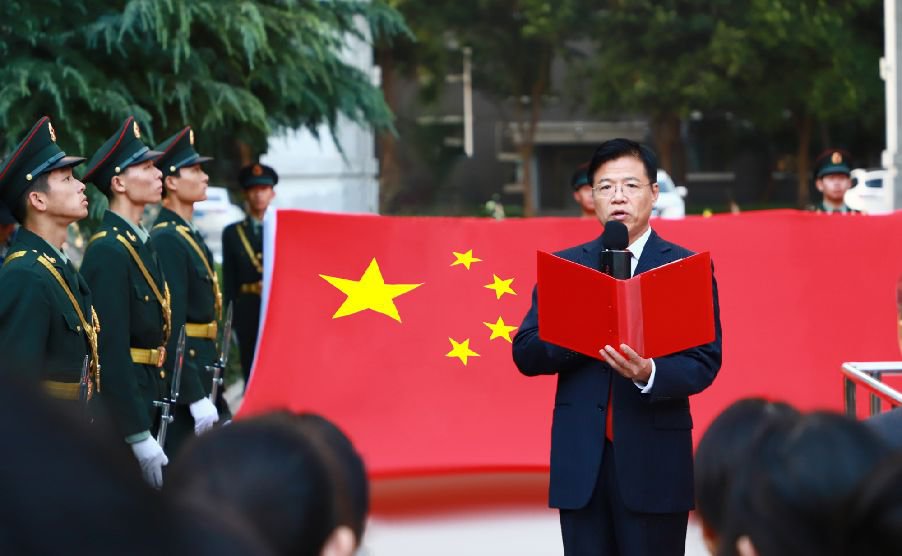對(duì)很多人來說,魯迅先生的雜文是匕首,是投槍。一句話,他的雜文總是在“戰(zhàn)斗”。人們說魯迅的雜文尖銳辛辣,并且在這些尖銳辛辣的文章背后,站著一個(gè)邊讀馬列、邊做雜文的“海歸”在傲視著國(guó)民黨反動(dòng)派。
這種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或許是對(duì)的。自然,魯迅是革命的魯迅,魯迅的革命也是浸入骨子里的革命。但是,因?yàn)槠涓锩膹氐?,魯迅先生的文章反倒顯得不那么劍拔弩張,相反,倒是在“嬉笑怒罵皆成文章”之時(shí),筆墨中流露出關(guān)愛世人的溫暖情懷,并不是那么具有“戰(zhàn)斗性”了。因?yàn)樵隰斞赶壬磥?,革命之革,不是要把命革掉,而在于讓?guó)民“幸福地度日,合理地做人”,否則就只是“革命,革革命,革革革命……”。如果這樣無休止地革下去,城頭變換大王旗,根本不是革命的本意,而只是那些失去生命的革命者的悲哀。
魯迅先生的文章,更多的是希望在精神層面實(shí)現(xiàn)國(guó)民的思想革命。這種革命既溫和又猛烈,既因事而發(fā)又常駐人心。所以魯迅那些文章,我們今天讀來,依然覺得仿佛在說身邊事,對(duì)現(xiàn)實(shí)的關(guān)切涼徹背脊。
《導(dǎo)師》一文就是極好的例子。1925年5月15日,魯迅先生在自己編輯的《莽原》周刊上,以《編完寫起》為題目寫了四段話。這四段話后來分別以《導(dǎo)師》、《長(zhǎng)城》(收入《華蓋集》)、《編完寫起》(收入《集外集體》)為題再收入魯迅先生的文集發(fā)表?!秾?dǎo)師》這篇文章一開頭就寫到:“近來很通行說青年,開口青年,閉口也是青年。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論?有醒著的,有睡著的,有昏著的,有躺著的,有玩著的,此外還多。但是,自然也有要前進(jìn)的。”這幾句話單從語言來說,倒也并不十分嚇人。但是,我們要認(rèn)識(shí)魯迅先生,最好就是從這些看似平平淡淡的句子里去想象魯迅先生的形象。
時(shí)人有不少的文章都提及魯迅先生愛護(hù)青年,這當(dāng)然是不錯(cuò)的。單是從“青年”這個(gè)詞語的基本含義來說,恐怕主要的內(nèi)涵在于年齡段的劃分。但一個(gè)人的思想狀況和行為方式,卻未必總和年齡呈完全的對(duì)應(yīng)關(guān)系:老年人可以先進(jìn)得朝氣蓬勃,少年人也可以保守得老氣橫秋。所以,單單是從年齡意義上所講的“青年”,未必都是魯迅先生眼里“可以同懷視之”的“同志”。世間的萬象盡管復(fù)雜,但在魯迅先生的筆下,往往都顯得極其分明。當(dāng)然,這種清醒的認(rèn)識(shí)也讓他感到痛苦。“兩間余一卒,荷戟獨(dú)彷徨”。這個(gè)想要叫醒鐵屋子那些快要悶死的人們的清醒者,不得不面對(duì)一個(gè)事實(shí):這些昏睡的人們盡管有反抗者在,有些人卻甘愿在鐵屋中悶死,甚至有些人就是這鐵屋子的制造者和守護(hù)者。
因此,魯迅眼里的青年不能“一概而論”。因?yàn)榍嗄陚儾⒉欢际恰扒斑M(jìn)”的青年,乃是他所說的“有醒有睡有昏有躺有玩”的不同形象的青年。在《答有恒先生》一文中,魯迅先生說“我恐怖”了,這恐怖的原因,就是他發(fā)現(xiàn),居然是青年人在殘殺青年,而且手段之殘忍,是他始料未及的。他原以為壓迫殺害青年的人都是老人,而隨著這種老人的死去“中國(guó)可以變得比較地有生氣”,但是,現(xiàn)在他的“樂觀想法”有了很大的改變。事實(shí)上,魯迅先生對(duì)青年人的懷疑,也許倒不開始于《答有恒先生》。在《藥》這篇文章中,他對(duì)中醫(yī)的懷疑,對(duì)觀看殺人游戲的人們的國(guó)民性的懷疑,都說明他即使處在熱烈的情緒中,也始終保持冷靜的懷疑態(tài)度。但無疑,這種冷靜和懷疑需要思想家壓住內(nèi)心的奔騰之火,揆諸文字,便是文字中的“吶喊”,但是作者的心境,終究是沉郁而悲涼。
《狂人日記》的結(jié)尾,作者說要“救救孩子”。大抵孩子感染世態(tài)尚少,有救的必要,也有救的可能。對(duì)于養(yǎng)護(hù)孩子的成人來說,他們需要“自己背著因襲的重?fù)?dān),肩住了黑暗的閘門,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,此后幸福地度日,合理地做人?!边@是一件“極偉大要緊的事,也是一件極困苦艱難的事?!保ā督裉煳覀?cè)鯓幼龈赣H》)。孩子長(zhǎng)成青年,青年變成未來的中年和老年,在這個(gè)過程中需要合格的父親,需要合格的教導(dǎo)者。當(dāng)然,在“做父親”這個(gè)問題上,做到解放孩子又解放自己的人,恐怕并不占多數(shù)。至于教導(dǎo)青年,在20世紀(jì)開初幾十年的中國(guó),恐怕所謂“導(dǎo)師”自己也是大有問題的。當(dāng)然,并不是說20世紀(jì)開初的幾十年就沒有優(yōu)秀的“導(dǎo)師”,而是說,“導(dǎo)師”首先需要解剖自己,需要自識(shí)與反思?,F(xiàn)在許多人憧憬似地談?wù)撁駠?guó)時(shí)期學(xué)術(shù)界多么美好,恐怕也是在思想上容易患上懷舊病的緣故。社會(huì)固然可以把人變成鬼,也可以把鬼變成人,但就思想層面而言,一個(gè)人的思想境界倒未必都是“時(shí)代的反映”。在20世紀(jì)頭幾十年里,世事變幻莫測(cè),自然也少不了混水摸魚趁亂世得好處的所謂“導(dǎo)師”。即使“導(dǎo)師”沒有騙人的本意,卻往往屬于那種“灰色可掬了,老態(tài)可掬了,圓穩(wěn)而已,自己卻誤以為識(shí)路”的人,這種人“假如真識(shí)路,自己就早進(jìn)向他的目標(biāo),何至于還在做導(dǎo)師”。當(dāng)然,好的“導(dǎo)師”是有的。但魯迅先生之憎惡“導(dǎo)師”這類稱號(hào)和人物,乃在于“導(dǎo)師”的瞞和騙及青年人對(duì)“導(dǎo)師”的那種盲從。青年人需要自己思索,自己做主。否則,如果“導(dǎo)師”是糊涂蟲,那他開的書目也是糊涂書目,盲從“導(dǎo)師”的金字招牌的青年,則更是糊涂。在魯迅先生看來,青年人所需要做的,與其尋找什么“導(dǎo)師”,倒“不如尋朋友,聯(lián)合起來,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?!彼麄儜?yīng)該遇見森林便辟成平地,遇見曠野便栽種樹木,遇見沙漠便開掘井泉。如果非要尋找什么“導(dǎo)師”,便又會(huì)走上荊棘塞途的老路,不能開拓出新徑。
人性會(huì)不會(huì)變得更好,社會(huì)會(huì)不會(huì)變得更好,今天的人們都可以根據(jù)自己的經(jīng)驗(yàn)得出自己的回答。但我們需要清楚的是,魯迅先生并不反感真正有意引導(dǎo)他人成長(zhǎng)的“導(dǎo)師”。實(shí)際上,他自己就給許壽裳的兒子開過必讀書目,也到大學(xué)授課和演講,他也知道在一個(gè)迷茫的時(shí)代,精神“導(dǎo)師”的重要性。他所反對(duì)的,是迷信、浮夸和虛假;他所堅(jiān)持的,是在一個(gè)近乎絕望的社會(huì)中,幫助人們找到精神上的希望。
在社會(huì)的黑暗襲來的時(shí)候,很多人被沉重的車輪碾死、嚇?biāo)溃蛘咛颖?,或者幫忙推?dòng)這黑暗的機(jī)器,而魯迅先生所做的,是冷靜地觀察,沉穩(wěn)地揭露,他在絕望中尋找希望,在反抗中予世人以關(guān)懷——即使他自己所處的環(huán)境,黑暗得讓人窒息。